|
发信人: blue66666(风月) 整理人: zrjh1015(2004-08-09 17:58:33), 站内信件 |
| 文章标题:《又看见了什么?──谈《红楼梦》的性取向》
发表日期:2003年10月20日 出处:夜看红楼论坛 鲁迅先生在谈到《红楼梦》时,曾有这么一段话:“单是命意,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: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 那么还能看见什么呢? 一 《红楼梦》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古典小说,然而在西方世界,其流行程度远在《金瓶梅》,《西游记》,及《水浒传》之下。有些洋人,也算读过这部著作,仿佛猎奇多于欣赏,提出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:“贾宝玉如此女性化,会不会是个同性恋者?”不知是他们特别敏感呢,还是我们东方人在他们眼里,都有一种女性化的气质,令人想入非非。他们的问题出自于他们的印象,但要回到得好,决非Yes or No所能对付得了的。 “行为偏僻性乖张,哪管他人诽谤!”一句话,概括了贾宝玉性格上引人注目之处。他是一名从“膏粱锦绣”中成长出来的贵族公子,但他与一般的纨侉子弟又有不同的地方。贾宝玉钟情于珠闱翠绕,在大观园中,他是唯一的男性主子。对女性,宝玉的评价也颇有玩味之处,他认为,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男人是泥做的骨肉,又称“天地灵淑之物,只钟情于女子。”一个男子如此看待女人,仅仅用“尊敬与同情妇女”是解释不通的,更扯不上“提倡男女平等,反对封建意识”。说白了,他不愿当男人,要当女人! 自然,上述的行为言论,毕竟与“性取向”还是有区别的。有的读者会提出,在《红楼梦》中,写得明明白白,贾宝玉初试云雨,是与他的贴身丫环──袭人,难道他们俩同性。 宝玉与袭人发生性关系的故事,是小说第五回“神游太虚境”的铺垫,而此一回目,又是整部作品的一个框架。所以,有必要将其有关情节作一陈述: 那日,宝玉随贾母一干人园中赏花,一时倦怠,由贾蓉之妻秦可卿照应到她的房中歇息。秦氏卧房里的一联一画,以及种种摆设器物,全用假托,出自于历史上著名的香艳故事,暗示色情陷阱。贾宝玉刚进房中,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来,顿觉眼蒙骨酥,昏昏睡去。梦中,由警幻仙子引路,进入了太虚幻境。在那里,宝玉看遍了金陵十二钗的图册,判词;而后,他又被仙子送入一香闺绣阁。阁内,警幻仙子向他进行了一番有关于世间巫山之会,云雨之欢的泛泛的说教言毕,话锋突兀一转,她指着宝玉道:“尔汝则天份之生成一片痴情,吾辈推之为意淫。唯意淫二字,可心会不可口传,可神通而不可语达。”又道,意淫于世道中“未免迂括怪诡,百口嘲谤,万目睚呲。”为了解救宝玉,警幻将其妹可卿许配于他,让他从此改悟前情,“留意于孔孟之间,委身于经济之道”。说罢,便秘授以云雨之技,推宝玉入房内,将门掩上自去。那宝玉,也便恍恍惚惚,依警幻所嘱,与可卿行起儿女的事儿来了。 这一大段写得极其晦冥,又带有强烈的嘲讽,真话假话,正说反说,颠来倒去,确实不怎么好读。犹如吃鸡翅,非得剔除零零细骨,方品得其味。警幻到底是警幻,她点明了,宝玉的“淫”与众不同,宝玉的“淫”于世难容,为了让宝玉改邪归正,她要宝玉与可卿成亲,甚至连作爱的技巧,仙子也未忽略。文中用了“密授”,“推”,“关门”等几个动词,把宝玉送入迷津。于是呼,梦中的宝玉便与梦中的可卿有了一番云雨。至于袭人,她只不过在宝玉梦醒过后,被宝玉照着梦里的法子,依样画葫芦,试了那么一番。此时的宝玉,于其说是在作爱,还不如说是在当学徒试更为合适。 按照常理,当一少年到了青春期,由于性激素的分泌,有了性欲,同时也有了性的“本领”,功到自然成。当然,从总体而论,确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需要性的“启蒙教育”。但是,警幻在梦中所担任的角色,决不是“性启蒙”,而是施展其大能,全方位地把宝玉变过来,纳入正统且正经的途径。在这一章回中,宝玉失去了小说前八十回中的聪慧和灵通,如同玩偶一般,受人摆弄。令人可悲,又令人可怜。 然而,就接在此章之后,犹如云开日出,在宝玉面前,出现了一名小生。他长得眉清目秀,粉面朱唇,身材俊俏,举止风流,“似胜宝玉一筹”。此人便是秦可卿的义弟秦鲸卿,字秦钟(音谐情种)。书中写到,宝玉自一见到秦钟,痴了半日,若有所失,叹道:“天下竟有这等人物!如今看来,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”两人你言我语,十来句话,便亲密起来。宝玉对下人说:“我们两个又不吃酒,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,省得闹得大家不安。”此后,有关宝玉与秦钟的两情缱绻,作者是这么描绘的,“因他二人这般亲热,也怨不得同窗人(指学堂)起嫌疑之念,背地里你言我语,诟谇谣诼,布满书店内外。” 书中宝玉与秦氏姐弟的关系,一梦一真,一晦暗一明亮,一被动一主动,造成天差地别的对照,贾宝玉的本来面目,还不昭然若揭了吗? 秦氏姐弟在红楼梦里仅仅昙花一现,两人不久都不明不白地死去,好象作者塑照这两个人物,为地就是佐证贾宝玉的“性取向”。好歹,秦可卿还得了一支曲子,曲名意味深长──“好事终”。 二 讨论《红楼梦》,不能不涉及到林黛玉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不朽,独树一帜的林黛玉形象占了相当大的成份。宝黛的爱情悲剧,早已成为文学经典而论,也是家喻户晓的故事。若要做贾宝玉“性取向”的文章,很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。 开卷《红楼梦》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神话的叙述:女娲补天时留下一快石头未用。天长地久,石头修成人形,名为神瑛侍者。侍者常在灵河岸行走,见河岸边有一株绛珠仙草,逐日以甘露灌溉。仙草幻化,为一女体,她心思想,既得神瑛侍者甘露之恩,若下世为人,欲将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,还得过了。 这个神话故事,便是宝黛关系的提契。宝玉将黛玉视为知己,看作同类,甘露滋润,惜心护呵。而林黛玉呢,她唯有将自己柔弱生命中惺惺相惜之爱,化为泪水,报答于宝玉。一首“枉凝眉”道出两人的缘份:“一个是阆苑仙葩,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,今生偏又遇着他;若说有奇缘,如何心事终虚化?”他俩,是灵的相投,是美的契合。他们注定得不着姻缘,也不屑于姻缘。 这也便成为《红楼梦》与《西厢记》,《牡丹亭》的相异之处。后者的主题相当明了,是情欲的追求与封建礼教的捆绑之抗争。莺莺对张生,由情到欲;杜丽娘对柳梦梅,由欲到情。情和欲的不可遏制,均被作者在本子中抒发出来。也正因此,这两本书被封建士大夫斥责为“淫词艳曲”。不否认,《红楼梦》中也有所谓的“淫词艳曲”,但在宝黛之间,绝无任何不洁的描写,作者死守住“洁本洁来还洁去”,宛如一道清流在贾府的污泥浊水中流淌。 小说的第二十三回,宝玉和黛玉在大观园内收拾落花,又一同偷读禁书西厢,为书中人物的互相爱慕而心动神摇,如醉如痴。该段落,写的十分美,很多人都熟悉,也一直作为重要情节,引证这两位青年男女冲破束缚,悄悄地恋爱。但如若我们有心地浏览,便会觉得不象那么回事。他俩喜欢西厢,因为在他们眼里,西厢真是好文章,词句警人,余香满口。但西厢记里的爱情表白,却被他们用来相互斗趣。特别是宝玉向黛玉求饶的那段话,疯疯傻傻,令人忍俊不禁:“好妹妹,千万饶我这一遭吧,我要有心欺负你,明儿我掉在池子里,叫个癞头鼋吃了去;变个大王八,等明儿你做了一品夫人,病老归西的时候,我往你坟上驼一辈子石碑去。”宝玉赌咒发誓,怕林妹妹受委屈,竟然把林黛玉嫁到人家那里去当“一品夫人”去了,你看荒唐不荒唐。后来,林黛玉因误会可真受了委屈,独自葬花,且泣且呤,好不伤感,也正到了多情公子贾宝玉表态的时机。但他这个人,在林姑娘面前,一点子装腔作势也不会:“谁知你忽然不理我,叫我摸不着头脑,少魂失魄,不知怎样才好,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,任凭高僧高道忏悔,也不得超生,还得你说明了原委,我才能托生呢!”这番话,说得极其关键,贾宝玉对林黛玉,是作为知音来追求的。他把整个心怀都向她畅开,字字饱含着真情。宝玉四周的美女花团锦蔟,他衷情于黛玉,为“淫词艳曲”。不否认,《红楼梦》中也有所谓的“淫词艳曲”,但在宝黛之间,绝无任何不洁的描写,作者死守住“洁本洁来还洁去”,宛如一道清流在贾府的污泥浊水中流淌。 小说的第二十三回,宝玉和黛玉在大观园内收拾落花,又一同偷读禁书西厢,为书中人物的互相爱慕而心动神摇,如醉如痴。该段落,写的十分美,很多人都熟悉,也一直作为重要情节,引证这两位青年男女冲破束缚,悄悄地恋爱。但如若我们有心地浏览,便会觉得不象那么回事。他俩喜欢西厢,因为在他们眼里,西厢真是好文章,词句警人,余香满口。但西厢记里的爱情表白,却被他们用来相互斗趣。特别是宝玉向黛玉求饶的那段话,疯疯傻傻,令人忍俊不禁:“好妹妹,千万饶我这一遭吧,我要有心欺负你,明儿我掉在池子里,叫个癞头鼋吃了去;变个大王八,等明儿你做了一品夫人,病老归西的时候,我往你坟上驼一辈子石碑去。”宝玉赌咒发誓,怕林妹妹受委屈,竟然把林黛玉嫁到人家那里去当“一品夫人”去了,你看荒唐不荒唐。后来,林黛玉因误会可真受了委屈,独自葬花,且泣且呤,好不伤感,也正到了多情公子贾宝玉表态的时机。但他这个人,在林姑娘面前,一点子装腔作势也不会:“谁知你忽然不理我,叫我摸不着头脑,少魂失魄,不知怎样才好,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,任凭高僧高道忏悔,也不得超生,还得你说明了原委,我才能托生呢!”这番话,说得极其关键,贾宝玉对林黛玉,是作为知音来追求的。他把整个心怀都向她畅开,字字饱含着真情。宝玉四周的美女花团锦蔟,他衷情于黛玉,并不在于她是美女中的一员,更确切地说,并不在于她身为女儿。他爱她,因为她是他人生相知相投的伴侣,对功名仕途,世嗣昌隆,他们有一致的思想基础。旁人的正统观念,在他们看来,不过“混账话”而已。两人平常说的话“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要恳切”。正因为如此,莫要说在贾府,就是在整个社会上,他们被视为离经叛道,不肖种种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们无比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,升华到精神上难舍难分的相爱境地。就如林黛玉所感叹的那样:“黄金万两容易得,知己一个也难求。” 可惜的是,在高鹗后续的四十回中,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戏剧化场面,调包结婚。一下子,格局大变。于是呼,林黛玉对贾宝玉,由爱及嫉,由爱及恨,眼泪不再流,变成了恶狠狠的叫骂。数声“宝玉,你好,你好……”林姑娘离开了人世。世俗的嫁娶,包办一切,也将这部巨著的精髓扫荡而尽。宝黛二人,一个要娶,一个要嫁。作得死去活来,闹得天昏地暗。虽然,高氏的续作,一直被红学家们讥为“狗尾续貂”,无奈狗尾太长,占了貂身的一半,又是最能甩动煽情的。此外,虽然,高鹗在气质与才华上无法与曹雪芹比,但他深悉如何迎 合读者,也就由此而站住了脚。当年,上海的徐玉兰与王文娟演的宝哥哥和林妹妹,其中最催人泪下的“黛玉焚稿”,“宝玉哭灵”,还不就是从那条“狗尾”上甩出来的。一时间,马路弄堂,会唱绍兴戏的及不会唱绍兴戏的,都在大呼小喊:“林妹妹,我来迟了,我来迟了哇!”喊得让人心发颤。天哪,一出悲剧本不是这般样发生的。断送这两名青年的,不是贾母,王熙凤与薛宝钗,也怨不得高鹗,世俗观念本身就有它天经地义的权威性。 《红楼梦》问世后二百五十年,有一出电视连续喜剧,曾经创出了美国电视剧最高收视记录,还获得了艾美奖,那就是大家熟知的《Will and Grace》。精心的编排,生动的故事,出色的表演,赢得各阶层的喜爱,同性恋者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友谊,心悦诚服地被人接受了。再想想《红楼梦》,留下的恐怕便该是一声微微的叹息:换了人间! 三 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,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;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,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” 好一支缠绵悱恻,风流儒雅的曲子。寄托了少年的怀春,抒发了对心上人的眷恋。唱此曲的是宝二爷──贾宝玉,地点在将军之子冯紫英的宴会上,在座的为一档子富贵闲人,唯有一位,地位卑微,忠顺亲王府的戏子,此人便是宝玉吐露爱慕之情的对象──蒋玉菡。 蒋玉菡,又名唤琪官,书中出场不多,但不可小看。他的名字中也有个玉字,姓氏带草字头,似乎也响应了木石良缘(众所周知,木石良缘应指林黛玉)。可见,在作者心目中,蒋玉菡非等闲之辈。两人初次见面时,宝玉见他妩媚温柔,十分留恋,向袖子中取出扇子,将一个青玉扇坠解下,赠于他。蒋玉菡则将系在小衣儿的一条大红汗巾解下,这汗巾是北静王的赠品,西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,名贵非常,玉菡将此回赠宝玉,“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。”两人互赠表记。在秦钟去世之后,贾宝玉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,其命运的玄机也由此而 发。 必须指出的是,蒋玉菡不是林黛玉,无论从才学修养,还是从性格品味,他都难以与宝玉匹配,他是个进不了红楼的红楼梦人物。蒋之所以得到宝玉的青睐,唯一的原因,他们是“同志”。因而,他们之间处于一种斯混状态。为了瞒住贾府上下,也为了躲避忠顺亲王府的鹰犬,在东郊离城二十里一个叫紫檀堡的地方,便是他们的幽会场所,也成了这二人的天地。这紫檀堡的房产,究竟是蒋玉菡所置,还是宝玉为“金屋藏娇”花的银两,书中没有交代。有人认为被后人删去,但也无关紧要。无论怎么说,宝玉与蒋玉菡的亲密的同性之爱, 已确定无疑,并传扬出来,弄得这一域内“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在说,他(蒋玉菡)近日与衔玉的那位令郎相遇甚厚。”为此,忠顺亲王府派长官到贾政处索人,贾政得知,气急败坏,眼都红了,在他看来,宝玉干的勾当,若如可饶,日后可为杀父杀君之罪!贾政将孽子大加鞭鞑,打得宝玉由腿至臀,或青或紫,或整或破,竟不见一点好处。 值得提出的是,宝玉受责后,有一段黛玉探访的情节,不过短短几行,却感人肺腑,牵人思绪。书中道: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,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,气噎堵喉,更觉厉害了,心中提起万句言语,要说时却不得说得半句。半天,方抽抽噎噎地说:“你可都改了吧!”宝玉听说,便长叹了一声道:“你放心,我便是为这些人死了,也是情愿的。” 林黛玉,“心较比干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”,贾宝玉有“断袖之癖”,凭她的敏感与聪慧,不可能不觉察。依常人之见,他两是一对恋人,男友有外遇,并闹腾了出来,一般作女友的会怎么样,不难想象;更何况林妹妹,不病死,不气死,自己也会去寻死,(续书便是照此逻辑发挥的)。然而,此时此刻,面对她唯一可亲近的人,这位柔弱女子,伤心惨目,泪流不止,不是为自己,丝毫不是,而是为了宝玉。用眼泪报答恩爱的神话,在此得到了印证。所谓“改了吧”,与其称为规劝,还不如说是为爱人担忧。自古以来,林黛玉一直被视为“妒忌”的化身,有一位学者在论妒忌时,将奥赛罗,林黛玉与周公瑾三人比作妒忌的典型。可怜她,狭置于两名强悍的男人之间,担当同等的指责,实在太不公平。这里存在有相当程度的误解和偏见。林黛玉多愁善感,个性孤独,言辞尖利,均为不争的事实,后四十回里,又有了大大的走样。但是,林黛玉是一位非凡的女性,她对于宝玉的爱,不附带任何条件,是舍己的。面对无情的封建势力的棍棒,她把内心深处的爱,化作串串泪珠,奉献在宝玉面前。宝玉的一声:“你放心吧。”便是她最大的慰藉。正因为如此,这两个人才可能携起手,坦坦荡荡的我行我素,成为一个时代的叛逆者。 相对之下,宝玉与蒋玉菡的恋情就达不到那种境地。写到此处,不由令我阵阵胆寒。是不是因为圈子狭小,是不是圈内的人都有一种悲凉的怪异,为什么圈内的交往大多停顿在“游戏人生”的水平。宝玉从蒋玉菡处得到的,不过是一条大红汗巾,尽管这条汗巾来历不凡,又相当名贵。 四 张爱玲先生说过,所谓的三大恨事,一是鲥鱼多刺,二是海棠无香,三是红楼梦未完。《红楼梦》写到八十回,断了,断得斩钉截铁,到底是怎么回事? 把《红楼梦》当小说来读的人,提出了他们的论断,曹雪芹突然撒手归天,死因不是心肌梗塞,便是脑中风,不然的话,何至如此苍促,《红楼梦》的后事都未来得及细细交代哩。 但是,把《红楼梦》当作梦来对待的人,却有另一番见解。他们说,曹雪芹从梦中醒过来了,梦是无从继续的。哪见过有哪个梦能完完整整,有头有尾。“沉酣一梦须终醒,冤孽徒消好散场”。没有结局,便成了结局。 曹雪芹醒了,他推开了案前的纸,把手中的笔甩得老远老远,笔尖在茅屋的灰墙上,流下了一串鞭打般的墨迹。他长呼一声:“罢也!”就此将一切停于一个定格。 曹雪芹之所以不往下写,他心中明了,贾宝玉的“祸根”,如同他佩的灵通宝玉一样,是从胎里带来的。他根本就不可能“改邪归正”。或许,他会姑且迫于家族的压力,与表姐薛宝钗接为“金玉良缘”。“叹人间,美中不足今方信,纵然齐眉举案,到底意难平。”作为小说,又往下交代了一步,再往下呢?作者实在推测不了,社会势力能够宽容他多少。在前八十回里已有暗示,贾府大厦忽喇喇倾倒之后,贾宝玉与蒋玉菡的“丑祸”再发,宝玉铛锒入狱,这个情节,不可能如小说前半部那样,点到为止,必须正面阐述。如果将此事这般托出, 他有几分力气来招架洪水猛兽样的“应罪应悔”的指责?况且,“文字狱”的大门,一直对着他们这样离经叛道的文人虎视耽耽。匪夷所思,搁笔便乃为上策。 同时,曹雪芹也无意于在贾宝玉和蒋玉菡的关系上多下笔墨。这两位走到一处,无非为了人欲凡情。他们之间迸发不出灿烂的火花,只可能在现实中抖落出一个个浮躁的矛盾。这样,一部可称之为广阔时代画卷之巨著,一下子变成了《品花宝鉴》似的言情小说。作者极不情愿,读者也会因此而失落。好就好在,曹雪芹在他的文稿里打了伏笔,蒋玉菡在宝玉入狱之际,娶了袭人为妻。这两个曾与贾宝玉发生过肉体关系的男女结为夫妻,既是别具匠心的策划,又是合情合义的安置。 曹雪芹搁笔了,他写尽了贾府的荣华富贵,再写它的衰微破败,触景生情,感受到的,将是不堪的折磨。当时,他处于“绳床瓦灶,举家食粥”的境况,唯一的爱子的夭亡,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他无力再把笔提起,重新回到梦里去。以后的事,要往下写,一字一滴血,不罢也得罢! 顶顶要紧的是,他不忍心触笔于宝玉和黛玉的结局。这两个年青人相亲相投,脱离了尘埃的污染,超越了世人的企盼,进入了灵爱的境地。对于林黛玉,一位忧患于“一年三百六十天,风刀剑霜严相逼”的小姐,早逝是必然的。叙述她的早逝,是一件残酷的事。她眼中,“能有几多泪珠儿,怎禁得,秋流到冬,春流到夏。”宝玉惹祸上身,黛玉望穿秋水,不得音信。她终日悲啼,泪尽而逝。从而,还却了她人生的宿愿。这是不少红学家认定的线索的走向。可以想象得出,读者读了之后,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反映。当然,人们同情,会怜悯,会陪著书卷抹泪。但掩卷之后,理性也就掩盖了感性,七嘴八舌的议论和判断,会如潮如涌,说她犯践,自作自受,闹得鸡飞狗跳。林黛玉生前习惯了孤独,移情于清静;料想不到,死后还不得安宁。如果到了这部光景,埃怨的就不是贾宝玉,而是他曹雪芹了。 再看看贾宝玉,他的故事,实际上也用不着加以铺张了。宝玉的出走,看来是既定的结局,即使是高鹗,也不得不照此承接。他出走了,他身后的那片土地,原本凤尾森森,龙呤细细,好一派昌明盛隆,花柳繁华;如今,只留得一个白茫茫的大地。他枉落红尘若许年,终于又步出红尘。林黛玉的魂归离恨天,使他失去了对红尘仅有的怀恋。问题在于,他走往何方?都在说,他出家当了和尚,佛身升天。我终不信,我不信贾宝玉挣脱了身上的枷锁,又会自觉自愿地把另一付戒规套到脖子上。天命,他不得不从,尽管天命弄得他家破人亡,身败名裂。但要他从僧从道?我想,他决不可能依就!有一首曲子,曾在《红楼梦》二十二回里出现过,我想用过来证明我的观点,也作为本文的结束: “漫拭英雄泪,离别处士家。谢慈悲,剃度在莲花台下;没缘法,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,来去无牵挂。哪里讨,烟蓑雨笠卷单行?一任俺,芒鞋破钵随缘化。” ----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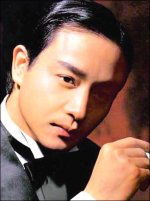  |
|
[关闭][返回] |